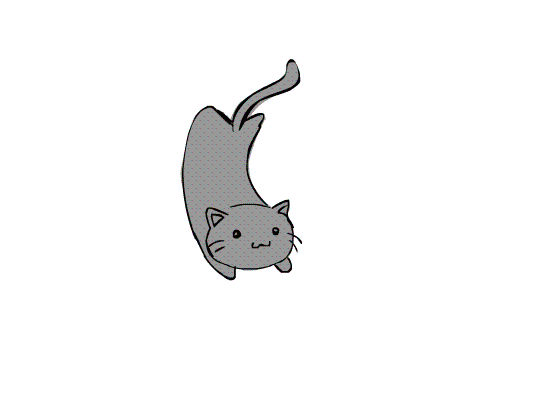YS
我有预感我会在最近死去。
这显然不是我第一次如此的预感,现在是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晚上22:10。
但是没人知道死亡究竟何时会到来。无论怎样的呼号呐喊在最终的结果揭晓前都是出神入化的演技。都不被人重视。我常常忘了吃药。就在昨天我一天补了两天的药量。不得不说,骤然停药很难受,补药也很难受,补了药才能保证数量上完美的精确,才能为这出戏提供完美的细节上的真实。除此之外由于唇裂,我已吃了五天各类维生素,今天6粒B6,6粒B2,6粒C,昨天6,7,7,前天停药,大前天8,13,6,再向前5,11,6,再向前6,15,7。吃药一周好,不吃药得7天。药已然在我生命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每天光是吃药就得花上几分钟。柜子散落着六七瓶大小不一的药,拆封与未拆封。桌面上滞留着CM老师送给我的只留下几粒的一盒松子,下面是由于寒冷而暂未表现出腐败的橘子。但是我将如何死去。
他在桥上走过便会把眼神淹没在水里。水泛滥着深绿色。没有轮渡掠过。岸边沉睡着深埋着自己的悲伤的灵魂。栏杆是那么浅,是那么充满信任的高度。然后某人从桥上落下,在某个清蓝色浸润的凌晨,在所有人的视野还没被将消逝的月亮照亮之时,激起轰鸣的水花。又或许是在某个深夜,在点缀着暖色残灯的新教大楼东侧九楼楼梯口,在那灯暗了又亮,亮了又暗的数次之后,在那从视野的边境的下一楼飘来的幽灵的恐吓下,从窗口,一跃而下,然后给大地泼溅血红色的墨点。直到凌晨被阳光扫去纯黑色外套下的遗体。又或许是在某个空旷的教室,当无形的寒冰块塞整片区域,他窒息地用锁链将门把手与脖颈相连,然后和多年前一样,和多年前一模一样,听见耳边自己的心跳,看见眼前逐渐发黑的世界,感触到四肢的麻痹和充斥脑部的眩晕。又或许是重新启用那封藏多久的刀片,干净利落,给天花板一口唾沫。但或许不再是使用过量的喹硫平,除了平添困意没有任何致命风险,如同带着安全绳的蹦极。也或许不再是无数刀轻微伤。
显然的事是,孤单并没有彻底的包围我。正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令我在正反两方面中撕裂,而我必须选择某一方才能够获得平静,才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此时我更倾向于彻底的自我封闭。正在昨天。我彻底的封闭了恼人的社交媒体,某种形式地拒绝了HSS老师的晚宴邀请。外人。她是外人。鸿门宴。鸿门宴。这是某种增进情感的方式。我拒绝。我拒绝。于是至少从上周日至现在,纵使被点名多次,我已然一言不发。但人们总是对得不到的留有期望。却又在得到后转为失望。我现在必须选择一方。无疑问的,我现在状态的崩溃仍然等待外部事件扣动扳机。这些就是我过去常常写到的所谓小事,即所谓未来有太多这样的小事了,而我却偏偏做不到这样的小事。因此我必须去死。
而我上述所写的一切,其意义生发于我非自然的死亡后。我现在所写的毫无意义。但是我真的有必要像前几封遗书那样交代自己的葬礼吗?难道死后的事物真的存在吗?不。动物性大脑的死亡决定了死后绝不存在灵魂等一系列事物。唯有心中的道德律那实践意义的理性在我心中阻止我那么做。但是你们为什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为什么我会如此被你们欺侮?
生与死果然是永恒的主题。爱与死也是。或许前者不仅仅指代爱情,也包括了亲人之间的爱。或许我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或许家人根本就不是我不去死的原因。或许没有我其他人都能够活得更好,或许我生命的戏剧可以在此就画上句点。或许我现在就可以退出世界上正演出的也是这世界上唯一正演出的戏剧,而永远也不知晓未来的事物。轮回在科学的意义上根本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相信轮回必然等同于抛弃逻辑。既然抛弃逻辑,那么一切假命题都有可能发生。在我退场后,场内将没有人知道我去哪了,我也永远不知道这丝毫不受某位配角影响的精彩的演出接下来的叹为观止的发展,这是一道可悲的厚壁障。但是,我的未来将异常精彩。我指的是我死后的世界。那是你们永远不知道的秘密。天堂与地狱都必然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脑海中存在,符合逻辑的事物已经预先取消了他们自身的存在。
我害怕明天的到来。我恐惧明天的阳光。我畏惧明天的空气。我多么希望明天永远像海市蜃楼般永远停留在明天,而今天永远像铁轨中轰鸣的火车,或是那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笔直的天墙,那永恒。
你的成就毫无价值。你所收获的毫无意义。你的存在从不被肯定。从未有人真正在意过你。从未有人真正考虑过你内心的想法。从未有人对你死心塌地。从未有人对你毫无保留。从未有人不在得到你如此的诘问后哭着喊着自己的真诚。从未有人不那样试图令自己感到的一塌糊涂。从未有人真正接触过你。从未有人真正看见过你。从未有人直视过你的眼睛正如你从不敢直视他人的眼睛。从未有人要求你保持安静,因为你太安静了。从未有人在要求你谈话时宽慰你放不下的心,而只是用可怜的收买,令你难堪,令你下意识对此的无数分析令你无所适从。从未有人要求你不要放下你的心墙。人们只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从不在乎你在想什么。从未有人肯握住你的手。从未有人。从未有人。你的周围从未有人。你的冷漠成为了你的拒绝。而你没有肯定。你只是沉默。你一言不发。你冰冷着。你孤单着。你在将自己杀死。你在吃自己的皮肉。你在喝自己的血。
而你所有的成就都将被一笔勾销。你的所有奖状,奖章,你的所有荣誉,你在人们脑海中所有崇高的记忆,都将被不复存在。不是被否定,而是不存在,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只是你所认为的存在。全是你脑海中慌乱的戏码。
他快要被这座大学给压死了。他受不了这庞大的机械体制和坚硬金属下血肉的脆弱身躯的疼痛。这二者似乎根本不相容,而没有任何共存的余地。现在是2023年12月28日星期四,中午11:56。他很早就拜读过那本薄薄的《逻辑哲学论》。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任何事件。我们的生命一如我们的视野是无限的。比起活人,逝者更令人感到亲近,而先贤的灵魂更是那么的鲜活,扑跃于一部部新印的著作上得以拥抱永生。他们灵魂已被洗至纯洁无暇。而生者的猜疑,顾忌,傲慢,疏离,令人作呕。肃穆的墓地,肃穆的墓碑,肃穆的铭文前那彩色的灵魂。他常常迷失在自然之中,无论是微雨飘摇下疏林小径中的迷惘,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骤雨新愁,百尺虾须在玉钩。无论是朦朦月色下苍朴石桥上的哀愁,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然后脑海被哀伤席卷,不能自已直到离开那个环境。
你离开埋葬着爱与梦想的故乡,回到冰冷的黑色天堂。转瞬而逝的梦境,你的灵魂散场。
无聊是多么宝贵的时光!在无聊之中,你体会永恒的苦楚,在迷惘之中,你寻觅冷清凄惨。白纸等待着被一切颜色泼溅所有的可能。时间的黑洞等待你去填满。虚无等待被充实。正因为一无所有,无聊拥有一切。
2024/1/21 18:32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干啥啥不行。
我在各种意义上不把自己当人看待。包括但不限于不给自己吃东西,伤害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不允许自己同他人交流,不允许自己睡觉,不允许自己盖被子,不允许自己在冬天把席子换成垫子,不允许自己洗澡,不允许自己刷牙,我在各种意义上不把自己当人。
直到现在,那几百粒扑尔敏仍然是只有我一个知道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心照不宣的秘密。当然他们没表示出来。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将永远记得妈妈在除夕夜为我点的允许我独自享用的两盒肯德基鸡架。那是我最最幸福的时刻。
或许,或许,或许,或许,或许,或许逃避也不会怎么样,就像无论如何都不会怎么样,无论怎么做都不会怎么样,即使按照这样来说杀人也不会怎样,但我只是做了我唯一敢做的也就是什么都不做啊。或许,或许,或许,或许,或许,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怎样,或许退学也不会怎样,或许死也不会怎样,在此所有事物的价值相同,所有事物也就都没了价值,或许,或许,或许,或许,或许,或许,或许这真的不会怎样,真的吗,真的吗,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假的,假的,但这应该真的不会怎样,因为你不是一粒沙我不是一粒沙吗,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我只敢跟你这张空白的无限的纸说话了。但我真的只敢这样做吗。对啊,对啊,就当我忘记了这回事忘记了补考这回事,不行吗,忘记了又是罪吗,我有罪吗?有吗?有吗?什么罪?撒谎???撒谎???非理性???还有21分钟补考就开始了,我的资料丢了,我的资料丢了,没人愿意了解我,但这不能也不配成为对他人的指责,因为他们爱我,因为没有人不爱我,因为他们爱我,但他们没有了解我,我的罪无非就在此处了,没有对爱我的人敞开心扉,我已经被诅咒了,或许我应该在我妈指责我的时候就立刻去死,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死和生难道有区别吗?生死难道有区别吗?为虚无主义建立意义无非是海上无根的高楼,虚无主义决定了不存在否决它的可能也决定了它不存在对外否决的可能,又有什么用?你又有什么用?你不敢找心理咨询师。在这方面上所有人的表现完美而不可挑剔,不可受到我的指责,那么这不就是都是我的错了吗,不应该有人为此负责吗,那不就只可能是我了吗?还有16分钟,你又能做些什么?你幻视了。你废了,和那说我妹妹废了的人渣不一样的废了,和那吃我猫的人渣一样废了,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一样,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还有十二分钟。现在没有人联系我。理论上,我可以一辈子不和别人说话。不是吗,没人愿意为了我牺牲,我也不配。我会被退学几乎是注定的。体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像过去几年我预言的那样成为压死我的稻草吗?我已经,和人们很疏远了。所有人。所有人。我死了。
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我恨死他们了。
我还真就感觉自己从没得到过他人的关爱,我的意思说,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有的,这是显然有的,这是不可能没有的,这是必然存在的,否则我早就死了,但是主观的角度看来,这不存在。我们之间,我与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之间似乎,总存在着一层或许是可悲的厚蔽障。这种疏离感,回顾这二十几年似乎从未不将我窒息。我似乎总是活在过去,而我看见备份的几年前的照片,那悲伤的申请仿佛他们已经活在了我所存在的现在,仿佛我自始至终永远被那层厚蔽障遮拦了和你们所有的人类的一切交流。仿佛我自始至终没有变过。我读到2015年也即近十年前的日记,我疯魔而不成活的精神状态仿佛从未改变过,那些终极的问题从那时起一直到达现在。但是你又有什么能力允许你这样彻底将你自我从人类的世界中切割。这必然是死路一条,也就是我已经走了很多年的路了。但是。人们又怎么会注意到我呢?注意到那从不注意到的人,不忽视自己已经忽视的事物,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我和我的童年时代仍在共享着同样的思维。那是一段稍有幸福的遗憾时光。终究啊终究,我的一切自戕终究不过是为了吸引人们的主意罢了,但我主观的何尝不是你客观的。无论我怎么说,我都在某种意义上的自戕,而无用提起目的了。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但要我去死也是可行的。没有完成的事就一定要完成吗?
每每想到现在的凄凉惨怆,我就会想起高考数学那道命运一般的排列组合。然后无比追念过去。我把它放太重了,所以拿不起来。而过去却已经被可悲的无可避免地染成渲色了。无论做什么。都。
我已经要为我的愚蠢崩溃了。
常言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无法否认的是,愁的相对意义上真的十分沉浓。
生活到目前为止真是一沓糊涂。而你之所以不这么认为,不过是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外还有自己的地方,还有其他事,正如我所拥有的之于孩童眼前的几片玩具。生活真是一塌糊涂。我的表达能力无疑问的下降了。我,我除了使用我之外还能怎么样开始一段句子?
一塌糊涂,就像沉没冰封着的海底已久,将迎来微弱的洞口的一丝光明,但是,从此,未来,彻底消散了,正如我的飘摇不定的未来,我的被这庞大的制度压死的未来。我愈发感到不安,不安,不安,不安,不安,不安,但孤单消散了。我已然习惯。多少年了。多少年了。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推心置腹,多少年了。我愿意吗?我被我自己所胁迫着而愿意了。但是要避免我的生活出现更多波澜的,专指那些不可控制,不为我所掌控的波澜的方法,只有成为正常的,标准的。只有尽可能让他们认为我在配合,只有这样。但我逐渐的,逐渐的,逐渐做不到了。去年上半年,有2021级的学长通过蓝桥杯省一等奖以特长生的身份转专业了。而我,而我。而我,而我,而我甚至直到最近才有这样的意识,即特长生转专业,可能性并非为0。这也就导致我避了去年上半年所有的计算机竞赛。我完全承担的了自费不报销啊。但是,为数不多的给予努力以实现可能的机会,真正的机会,就这么消散了,我只抓住它们消散着的尾巴。还有天梯赛,我也没有参加。我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都没有。根本没意识到我不可能,我不可能不转专业,我不可能,我不可能在这再待下去,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可能看着我所由内心深处令我流泪着的热爱的在我身边而不将它攫取入怀,我不可能放弃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而苟且,苟延残喘地在这度过这几年。具体来说,我来这纯纯粹粹是因为她分数线比较高罢了。还有可笑的不能出省。我真是糊涂了。搞得你现在很想回家似的。每次来回。都憔悴万分。十分草率的,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在这,在这个专业的未来。我纯纯粹粹是看见那较高的分数线,而想着或许从高分数线转低分数线会更容易而来这里的,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在当时,真是滑稽。可笑。你是谁?你这读我文字的人?我的秘密,终于在刚刚写下了。这或许是我第一次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的可笑的想法。我已经能看见那些人在笑了,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的但我必然会将之视为嘲笑的笑。也就是你的笑。真是幼稚啊。他们的影子叠加在那个冬季我因为搞错站队所依据的排名所依据的考试而被那发自纯粹喜悦的笑的来源的人影之中了。希望他能够成功。他没有我的污点。他能转专业成功。然后我的失败,,,,,,难道这连简称都没有的竞赛真的会有什么可笑的含金量么。你的机会在几个月前。与你擦脸而过了。你终究只是一个“人”。你也终究只是“一个人”。一个被迫的社会生物下疏远着的灵魂。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表现的是悲伤。但实际上是愤怒。很不解。
我都快不知道那三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了。不过说起来,或许去年以你低于目前你的水平的水平,什么竞赛啊也许还真赢不了。但这不过是没用的安慰。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我是真的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不仅是这,更是这个学校,更是这周围有人类存在的寝室,和永远不存在的隐私之类的。在这种意义上,班主任对我真的很好。可惜有点迟了。如果能早一点,如果能早一点,或许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的一切想法都是非常幼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孩子般的幼稚,我自以为是的东西实在太多,而盲于见到的太少。但,你们未必能看见我所看见的,即使你们能,你们现在也还暂时没有。我没法跟人交流,因而只能依靠先天给予的纯粹的某些原则来推断事物的发生转变。人类的世界太复杂了。这些原则早就被某些人和某些“人的组合”给折断了。因而我愈发难以理解你们了。而你。
而沉迷舒适圈本身就是十分痛苦的行为。而语言的孱弱令我无法准确表述。
我或许曾经真正的舔舐过死亡。在那虚幻的手腕手臂流逝的血光之外,那药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对这断言去除应该。但有什么用?谁没死过?!在此,我又消逝了。特殊。特殊。特殊。特殊。我不再特殊。这两个字真是我的耻辱。
我聊天的对象也就只有沉默的你了。你跟我一样沉默。准确来说,是我敢于与之聊天的对象。只有沉默的你。只有你不会诘问我。这样一改,准确多了。我拒绝了太多其他人了。
可怜的我啊,这世界上只有我真正的被你所接受了,也只有你是我真正所接受的了。我爱你所以伤害你。我杀了你所以解脱你。
我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阴郁?你恐怕,从没有,不害怕过。我还是害怕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害怕了。越来越害怕了。
我还是喜欢带有延迟的打字,而非实时的语言,模拟般的信号。
我已经失去很多很多了。绩点。绩点,,,,,,还有我的习惯。但我还有很多。愿我死后他们她们都能好好的。
当我发现可以毫无痛苦的幻想你们所有人的死亡,而无感触的时候。所以我挺难共情你们不想让我死的。
现在是2024/5/13 16:15:18,刚才转专业失败了。跟高考填志愿那时候如出一辙。我根本没有那个权利。这真的不禁让我想到我做的事的意义。计算机专业外的人的计算机水平超越了以计算机为专业的人。真没意义。我拿牌子有什么意义呢。制度下,只有荒诞的结果。荒诞的制度。我真适应不了这个世界的制度。制度而不是规则。一切努力都扑了个空。真是滑稽。可笑。
但我现在要谈谈我妈。我刚刚又回想起了她给我下跪那场面,仅仅要求我去游泳。将那和,昨天的她以她的死相要挟我不自杀,这样一对比,她就一点没变,她还只是个孩子,要求其他人必须满足她的孩子。她多久了还是一点没变。
我都不敢奢想我的未来了。牌子真有用么。没人告诉我是不是特长生仍然以其为前置条件。我不知道。我也永远不可能知道。ACM真的有意义么。我做的一切真的有意义么。它们都被否决了。都被否决了。根本根本根本根本根本不给我一丝机会。真想问候你们所有人祖宗。我啊。只有未来的我会可怜现在的我了。现在边上的人根本不理解我。只有未来的我能理解我了。我也只能跟你这张白纸聊天。没错,我自我孤立。
我恨我的辅导员。无理由的。
我没有朋友确实是因为我拒绝朋友。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我的错。这句话不带反讽。